咨询热线:
020-34385911
13316087099
微信预约:
13316087099

母亲的位置与心理咨询师的位置:一场内在张力的心理动力学探索
发布时间:2025-12-09
文|心理咨询师徐文娇
阳光透过窗户,在咨询室投下温暖的光晕。我的孩子,三岁多的小小孩,开心地从沙盘架上挑选玩具,给它们“做饭”、“沏茶”,扮演着有力的照顾者角色。这本是一个美好的陪伴时光。然而,一股莫名的焦虑在我内心升起。当孩子给三只小狗拿了两个盘子时,我动了,“几只小狗呀,几个盘子呀,我们数一数,一、二,是不是两个?还差一个呀?”
那一刻,我清晰地意识到,我当下的反应就是一个普通的母亲(充满责任与期望),而不是”工作状态中的心理咨询师”——节制、观察与跟随的专业人士。
而后,当孩子在25分转向另一个游戏——魔方。我心里咯噔一下,想起学校老师对TA注意力方面的提醒,心里开始担心“他是不是有注意力方面的问题?”“哦,好像还好,TA挺专注的”……
剩下的时间,
“妈妈,它怎么站不住呀?”
“妈妈,你帮我把那个拿过来”
“妈妈,我不想玩这样,我想玩那个”
……
50分钟下来,我早已摆烂——完全如同一个在露天公园的沙坑看孩子玩沙的妈妈,你爱玩什么就玩什么吧,不时欣赏、好奇两句;ok,玩完了,很好,收拾一下,走吧……
我不是一个咨询师,我的内心跟真正进行一场咨询完全不同!!!
这段经历,也让我思考:我们常说“买个沙盘回去跟孩子在家玩”跟真正的沙盘咨询是不一样,这里究竟有怎样的不一样,除了一个是具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和受训,一个是自学成材的父母,究竟还有怎样的不一样?
同样是面对一个在心灵象征世界中驰骋的个体,母亲的位置与心理咨询师的位置,究竟有何不同?双重身份切换的背后,“我”作为另一个在场的主体,有着怎样的内在体验?
一、双重身份切换的幻想与失去咨询师的位置
在陪伴孩子游戏的一小时内,是双重身份的切换吗?
坦白讲,很难做到。我更多的是在母亲的位置,无法把孩子当成真正的来访者,也忘记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——心理咨询师。
在那一小时里,我是TA的妈妈,TA是我的孩子,我投向TA的目光里带有社会性与发展性的目标——TA需要加强数学认知、TA需要更专注。
于是,在游戏中,母亲的目光越过了游戏本身的乐趣与象征,指向了“教育成果”:“这是几只小狗?”“需要几个盘子?”背后的意图是希望纠正认知、传授知识。游戏沦为达成教育目标的载体。
而咨询师的位置,则坚定地“以来访者为中心”,创造安全的空间,鼓励自性的发展,它是过程性的、体验性的。
咨询师不会将外部道德标准带入咨询室,其焦点在于跟随来访者(儿童)的游戏历程,好奇于TA内在世界“这些小动物在干什么呀?”“这只小狗是谁?”“这只小狗好像有些不开心”……这里没有对错的评判,只有对心灵自主探索的呵护与镜映。
二、焦虑淹没了中立与好奇
在母亲的位置,母亲关注的是孩子的社会表现,会对孩子产生社会评价。
比如,当孩子变换游戏,母亲立刻联想到学校老师对其“注意力不集中”的评价。这是母亲内在的焦虑——对孩子未来适应性的关切,也是母爱中保护性焦虑。
而咨询师的位置,则是努力保持“中立与好奇”。咨询师对行为现象本身感兴趣,而不急于将其病理化或简单归因。
孩子注意力的转移,在咨询师看来,可能是动力的流动,可能是潜意识的表达,
“TA刚才怎么了?”
“是受挫了吗,想要转移下主题,来缓解挫败感,或者TA 在喂养游戏力中体验到更多自我力量,借由这些力量,想探索更有难度的任务”
……
来访行为的变化,是需要被理解而非评判的现象。咨询师如同一张白纸,给来访者的真实体验留出空间。
三、行动干预与节制涵容
当孩子遇到困难,如玩具站不稳时,母亲的位置倾向于快速干预,以解除孩子的困境和可能的负面情绪。
母亲常直接上手调整,或提供解决方案,旨在恢复游戏的顺畅,避免孩子体验过多的挫败。这是一种直觉行动。
而咨询师的位置,则强调“节制”与“涵容”。
面对来访者的困境,咨询师的首要工作是情感镜映与命名,“对哦,它站不稳,你感到遇到困难了,是吗?有一点挫败,有点沮丧哦。”
通过语言为情绪赋形,帮助来访者识别和涵容自己的情感体验,慢慢转化情感。
咨询师不做直接解决者,而是陪伴、等待、将来访者体验到的未命名的、原始的情绪情感,言语化、命名化,陪伴TA涵容自己的情绪并发展出自我效能感。
如果来访的鞋子掉河里了,母亲是直接帮忙打捞,避免孩子碰水涉险,而咨询师则是把鞋子拿到来访者够得到的位置,陪他自己用棍子多次尝试自己打捞,最后为他的成功喝彩。
四、共生焦虑与保持界限
母亲与孩子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情感依恋与部分无意识的共生感。孩子的情绪很容易直接牵动母亲的情绪。
当孩子说“你帮我拿过来”,母亲的位置时,有时难以区分“孩子的需要”和“我认为孩子应有的需要”,在给与帮助与鼓励独立之间会晃动。
而咨询师的位置,则建立在适度边界之上。
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是专业的工作联盟,有明确的界限,比如,不能与来访有肢体接触;觉察反移情和付诸行动。
当来访说“你帮我拿过来”,咨询师是将非语言的部分语言化、无意识意识化。
“你想靠近/依恋一下我,想我帮帮你,是吗”
或者“哦,你生我气了,因为……现在用凶凶的语气说‘哼,你帮我拿过来,我才原谅你’”
或者“你觉得刚才你责备了我,现在让我帮你,如果我帮你拿,我愿意为你做点什么,我们好像和好如初了,是吗”
咨询师深切地共情来访者的情绪与需要,但这种共情是经过反思的,旨在帮助来访者理解自己的内在冲突与需要,而非直接行动化。
五、“我的孩子”与“独立的他者”
在母亲的位置上,孩子是“我的孩子”,我是我孩子的母亲。
母亲的视角难免带有“这是我的孩子,我希望他好”的主体性投射。孩子的表现与“我”作为母亲的自我认同感、成就感、价值感紧密相连——“我是一个还不错的母亲”。
而咨询师的位置,面对的是“独立的他者”——一个拥有独立心灵世界的来访者。
咨询师的任务是暂时清空自己的需要与期待,尽最大努力去理解并协助那个独特的主体。咨询师认同的是专业角色所要求的匿名性、利他性与服务于来访者福祉的伦理准则。
六、母亲的α功能和咨询师的α功能
比昂提出,成熟的照顾者(母亲)需充当一个“容器”,接收并消化婴儿投射出的无法忍受的原始心理碎片——即“β元素”(原始、混乱、未处理的感觉印象和情绪)。
通过母亲自身的思考与涵容,β元素被转化为可以被理解的“α元素”(经过消化、可被思考的情绪与体验),再返还给婴儿,使其逐步内化这种心智能力。
在母亲的位置,当孩子“不识数”、“注意力转移”,这些现象触发了“我”内在的焦虑——社会评价的压力(老师反馈)、对育儿“不够好”的潜在恐惧、对孩子未来发展的担忧等。
于是,“我”内在的容器功能、心智空间被挤压,自身焦虑以行动化——直接提问、纠正——来处理这些不舒服的感受。这同时也将未经消化的“β元素”(焦虑)又投射回到孩子那里,打断了孩子对游戏体验的深度探索与消化过程。
而在咨询师的位置上,理想状态是努力维持强大而稳定的“容器功能”。面对来访者游戏中的种种象征与行为,咨询师致力于涵容其中可能投射出的混乱、冲突与强烈情绪(β元素),不急于用解释或行动去化解,而是通过好奇的提问、情感的命名、陪伴的观察,尝试将这些原始的素材转化为可供思考与叙说的心理内容,促进来访者心智化能力的发展。
七、咨询师所创造的“过渡性空间”
沙盘游戏,是一种充满象征性的游戏,是一个精心构建的过渡性空间。在这个介于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之间的“过渡性空间”,儿童可以安全地体验全能感、创造意义、处理焦虑、整合爱恨和内在冲突。
但在母亲的位置,“我”在那一刻由于自身的焦虑,可能更接近“侵入性的母亲”,将外部教育目标、社会规范带入孩子自主创造的游戏中,侵入了孩子的过渡性空间,干扰了孩子利用游戏进行自我整合的过程。
孩子在沙盘游戏中,本是在处理喂养、照顾的主题,探索力量与关怀,这关乎其内在情感现实。而母亲位置的提问,将游戏强行拉向了外在认知任务,打断了其对内在世界象征性的表达与探索。
而在咨询师位置,则所有技术——好奇游戏内容、描述关系、探索叙事、命名情绪——其核心目的都在于守护和拓展这个过渡性空间,为孩子的创造性自我提供安全的抱持环境。咨询师愿意进入孩子内在象征世界,不引入外部议程,在跟随、镜映、澄清中,帮助孩子在这个空间里更自由地编织他的故事,表达他的冲突与需要,从而促进其真实自体的浮现和成长。
结语:
这场发生在沙盘室内的、悄无声息的“位置滑移”,让我更清晰地体验到,母亲的位置与心理咨询师的位置,是有不同的关系本质、社会功能和伦理要求。
“我”位置的滑移:作为母亲,与孩子共生、对其未来负责、承载社会期望的自我,在面对特定刺激(外界对孩子的评价、孩子发展性方面)时,其焦虑浮现,试图通过“侵入”和“指导”来掌控局面,缓解为人母的焦虑。
而作为咨询师,受过训练、致力于理解无意识、相信自主性的专业自我,倡导“节制”、“涵容”与“守护空间”,在沙盘室里,母亲身份所携带的原始焦虑与责任,淹没了咨询师角色所要求的反思性容器功能。
这50分钟的体验,让我更真实的体验到了心理咨询中双重身份的困难,以及“母亲身份”“咨询师身份”的不同功能。这场“位置”之思,也是一个珍贵的、思考的礼物,让我反思在咨询中,我真的稳稳坐在咨询师的位置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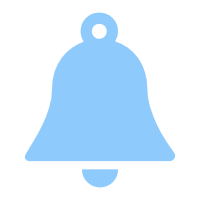 听说吧温馨提醒,如您遇到婚姻感情等困境时,请及时与广州婚姻心理咨询 m.020xlx.com联系,您的困扰有我们的专业帮助!
听说吧温馨提醒,如您遇到婚姻感情等困境时,请及时与广州婚姻心理咨询 m.020xlx.com联系,您的困扰有我们的专业帮助!
当您或孩子出现情绪、学习、行为、人际等心理问题,或你们的亲子关系出现问题时,请及时与广州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wap.020xlx.com联系,切勿延误而失去了治疗时机!
 热线:020-34385911、34371477, QQ937326707,微信:13316087099
热线:020-34385911、34371477, QQ937326707,微信:13316087099


